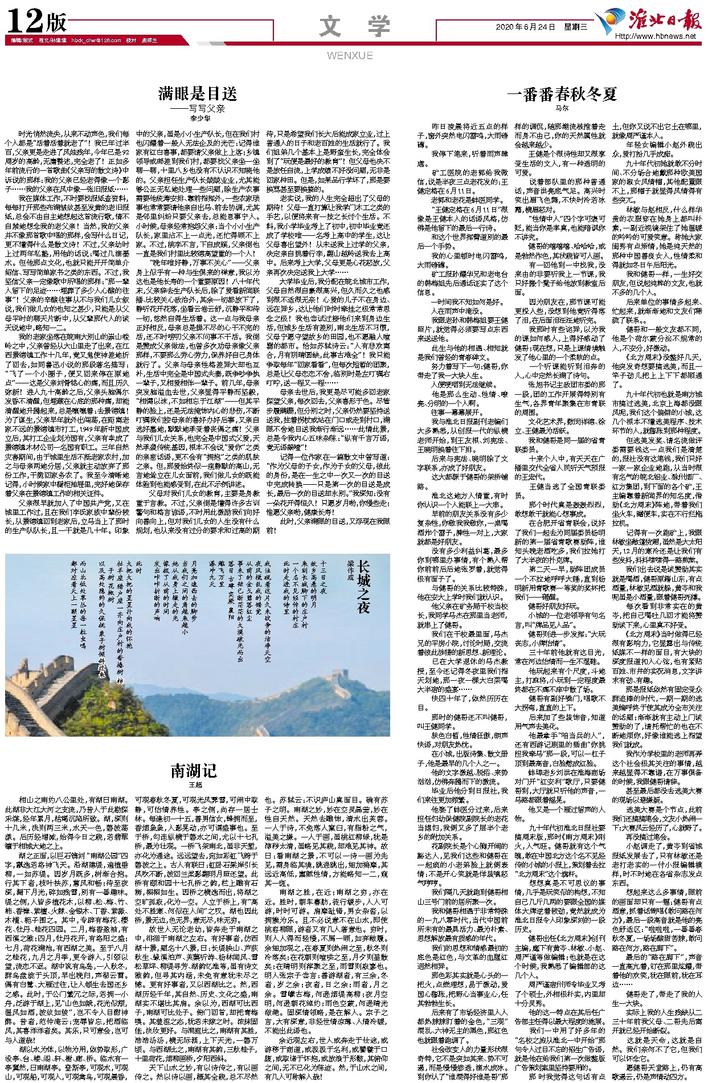马尔
昨日凌晨将近五点的样子,窗外突然电闪雷鸣,大雨磅礴。
我停下笔来,听着雨声肆虐。
矿工医院的老郭给我微信,说是半夜三点老花发的:王健定格在6月11日。
老郭和老花是蚌医同学。
“王健定格在6月11日”很像是王健本人的话语风格,仿佛是他留下的最后一行诗。
和这个世界挥臂道别的最后一个手势。
我的心里顿时电闪雷鸣,大雨磅礴。
矿工报孙耀华兄和老电台的韩梅姐先后通话证实了这个信息。
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
人在雨声中淹没。
我跟老孙和韩梅姐要王健照片,就觉得必须要写点东西来送送他。
此生与他的相遇、相知就是我们曾经的青春碑文。
努力着写下一句:健哥,你带走了我一大块人生。
人便哽咽到无法继续。
他是那么生动、性情、嘹亮、分明的一个人啊。
往事一幕幕展开。
我与淮北日报副刊老编们大多熟悉,从创报一代的纵横老师开始,到王友根、刘宪法、王晓明挨着往下排。
后来与宪法、晓明除了文字联系,亦成了好朋友。
这大都源于健哥的架桥铺路。
淮北这地方人情重,有时你认识一个人能联上一大串。
早前的朋友关系没有多少复杂性,你敬我我敬你,一桌喝酒炸个雷子,脾性一对上,大家就都是好朋友。
没有多少利益纠葛,最多你到哪里办事情,有个熟人帮你前前后后地张罗着,就觉得极有面子了。
与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他在安大上学时我们就认识。
他父亲在矿务局干校当校长,我同学马杰在那里当老师,就串上了健哥。
我们在干校最里面,马杰兄的平房小院,讨论时局,交流着彼此涉猎的新思想、新理论。
已在大学退休的马杰教授,至今还记得冬夜里我们指天划地,那一夜一棵大白菜喝大半宿的盛宴……
快四十年了,依然历历在目。
那时的健哥还不叫健哥,叫王健同学。
肤色白皙,性情狂傲,朗声快语,对朋友热忱。
在小城,出版诗集、散文册子,他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
他的文字激越、脱俗、来势汹汹,仿佛奔腾而下的激流。
毕业后他分到日报社,我们来往更加频繁。
他娶了蚌医分过来,后来担任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的老花当媳妇,我俩又多了层半个老乡的附加关系。
花副院长是个心胸开阔的豁达人,见我们这些和健哥在一起疯的小老弟脸上就俩表情:不是开心笑就是佯装嗔怒气哼哼。
我们隔几天就跑到健哥相山三号门前的居所聚一次。
我和健哥相遇于非常特殊的一九八零时代,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具活力、最为朴素、思想解放最有质感的年代。
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最初的底色是红色,与文革的血腥红迥然相异。
那色彩其实就是心头的一把火,点燃理想,易于激动,爱国心膨胀,把野心当事业心,任其勃勃生长。
后来有了市场经济里人人都热辣辣盯着的金色,“三观”混乱、六神无主的黑色,那红色也就跟着跑调了。
社会改变人的力量形状很奇特,它不是突如其来、势不可遏,而是慢慢渗透,滴水成冰。到你认了“谁混得好谁是哥”那样的调侃,随那潮流被推着走而身不由己,你的天然属性就会越来越少。
王健是个很诗性却又很享受生活的文人,有一种透明的可爱。
说着部队里的那种普通话,声音洪亮底气足。高兴时笑出眉飞色舞,不快时冷若冰霜,横眉怒对。
“性情中人”四个字可褒可贬,能当你是率真,也能暗讽你不讲究。
健哥的嘻嘻嘻、哈哈哈,或是勃然作色,其状貌皆可入画。
有一回他到一中找我,没来由的非要听我上一节课,我只好搬个凳子给他放到教室后面。
因为朋友在,那节课可能更投入些,没想到他竟听得落了泪,在后面泪汪汪地听完。
我那时有些诧异,以为我的课如何感人,上得好感动了健哥;现在想,只是上课情境触发了他心里的一个柔软的点。
一个听课能听到泪奔的人,心中定然长满了诗句。
张旭书记主政团市委的那一段,团的工作开展得特别有生气,各界青年聚集在市青联的周围。
文化艺术界,数闵祥德、徐立、王健最为活跃。
我和健哥是同一届的省青联委员。
十来个人中,有天天在广播里交代全省人民听天气预报的王宏代。
王健当选了全国青联委员。
那个时代真是轰轰烈烈,敢想敢干就能心想事成。
在合肥开省青联会,说好了我们一起去为同届委员杨明新的第一届省青歌赛助阵,谁知头晚老酒吃多,我们拉她打了大半夜的扑克牌。
第二天一早,助阵团成员一个不拉地呼呼大睡,直到杨明新用青歌赛一等奖的奖杯把我们一一砸醒。
健哥好朋友好玩。
小城的一位老领导有句名言,叫“牌品见人品”。
健哥则进一步发挥:“大玩丧志,小牌怡情”。
三十年前他就有这目光,常在河边怡情而一生不湿鞋。
他玩起来有个尺度,斗地主,打麻将,小玩到一定程度最终都在不痛不痒中散了场。
健哥有副好嗓门,唱歌不大拐弯,直直的上下。
后来加了些装饰音,知道用气声去美化。
他最拿手“咱当兵的人”,还有西游记剧里的插曲“你挑担我牵马”那一段,可以一杠子顶到最高音,白脸憋成红脸。
蚌埠老乡刘洪在淮海商场对门开“红安利”歌厅,只要健哥到,大厅就只听他的声音,一马路都跟着摇晃。
他又是一个雁过留声的人物。
九十年代初淮北日报社要搞周末版,那时《南方周末》刚火,人气旺。健哥就有这个气魄,敢在中国北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的小报上,策划着去拉“北方周末”这个旗杆。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几乎是玩笑似的构想,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要跟全国的媒体大牌逆着较劲,竟然就成为淮北日报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历史。
健哥出任《北方周末》创刊主编,麾下有黄岑、林敏、小赵、周严谨等做编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熟悉了编辑部的这几个人。
周严谨宿州师专毕业又考了个硕士,外相极朴实,内里却十分灵秀。
他的这一特点在其后任广告部主任得以最大程度的施展。
我们一中用了好多年的“名校之旅从淮北一中开始”那句令人过目不忘的招生广告语,就是他在给我们第一次做整版广告策划案里坚持要用的。
那 时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土,但你又说不出它土在哪里,就像周严谨本人。
年轻女编辑小赵外貌出众,爱打扮几乎成痴。
九十年代初她就敢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戴那种欧美国家的淑女风情帽,其他配置跟不上,那帽子就显得风情得有些突兀。
林敏与赵相反,什么样华贵的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叫朴素,一副近视镜架住了她温暖的吟吟的可爱笑意。称她大家闺秀有点矫情,她是纯天然的那种中国善良女人,性情柔和得就如冬日午后阳光。
我和健哥一样,一生好交朋友,但说起纯粹的文友,也就不多的几个人。
后来单位的事情多起来、忙起来,就渐渐地和文友们稀疏了联系。。
健哥和一般文友都不同,他是个荷尔蒙分泌不规常的人,不安分,好激动。
《北方周末》没整好几天,他突发奇想要搞选美,而且一竿子劲儿把上上下下都顺通了。
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南方城市搞过选美,北京上海都没跟风呢,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这几个根本不懂选美程序、技术环节的人,就膨胀到那种程度。
但选美发奖、请名流做评委需要钱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报社没有这笔钱,我们只好一家一家企业地跑,从当时很有名气的皖北铝业、滁州烟厂、红方集团,到下面的各个矿,王主编靠着新闻界的知名度,借助《北方周末》阵地,带着我们坐火车,蹭便车,实在不行拦拖拉机。
记得有一次跑矿上,我跟林敏坐敞篷货厢,虽然是大太阳天,12月的寒冷还是让我们有些发抖,抖抖嗦嗦得一路煎熬。
我们出去说是谈赞助其实就是喝酒,健哥原籍山东,有点酒量,林敏见酒就躲,黄岑和我呢虽是小酒量,跟着健哥死撑。
每次看到非常实在的黄岑,把自己喝吐几回才能将赞助谈下来,心里真不好受。
《北方周末》当时做得已经很有影响力,它显露出与传统纸媒不一样的面目,有大块的深度报道扣人心弦,也有紧贴百姓、市井的实况消息,文字讲求有劲、有趣。
那是报纸依然有固定受众群追捧的时代,一期一期的选美煽呼终于使其成为全市关注的话题;渐渐就有主动上门谈赞助的了,请托帮忙的也在不断地烦你,好像谁能选上指望我们就成。
我作为学校里的老师再弄这个社会极其关注的事情,越来越显得不靠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跟健哥请辞。
甚至最后都没去选美大赛的现场以避嫌疑。
选美大赛是个节点,此前我们还搞搞笔会,文友小热闹一下;大赛风云经历了,心就野了。
再没搞过笔会。
小赵调走了,黄岑到省城报纸发展去了,只有林敏还是老打老实的一付小报编辑模样,时不时地在各省杂志发点东西。
想起来这么多事情,眼前的画面却只有一幅:健哥有点酒意,抓着话筒唱《敢问路在何方》,最后一段高音就是他的亮色舒适区:“啦啦啦,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最后的“路在脚下”,声音一直高亢着,钉在那里炫耀,带着他的欢笑,犹在眼前,犹在耳边……
健哥走了,带走了我的人生一大块。
实际上我的人生残缺从二三十年前我父母、二哥先后离开就已经开始断裂。
这就是天命,这就是自然。我们奈何不了它,但我们可以怀念它。
愿健哥天堂路上,仍有高歌遏云,仍是声情动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