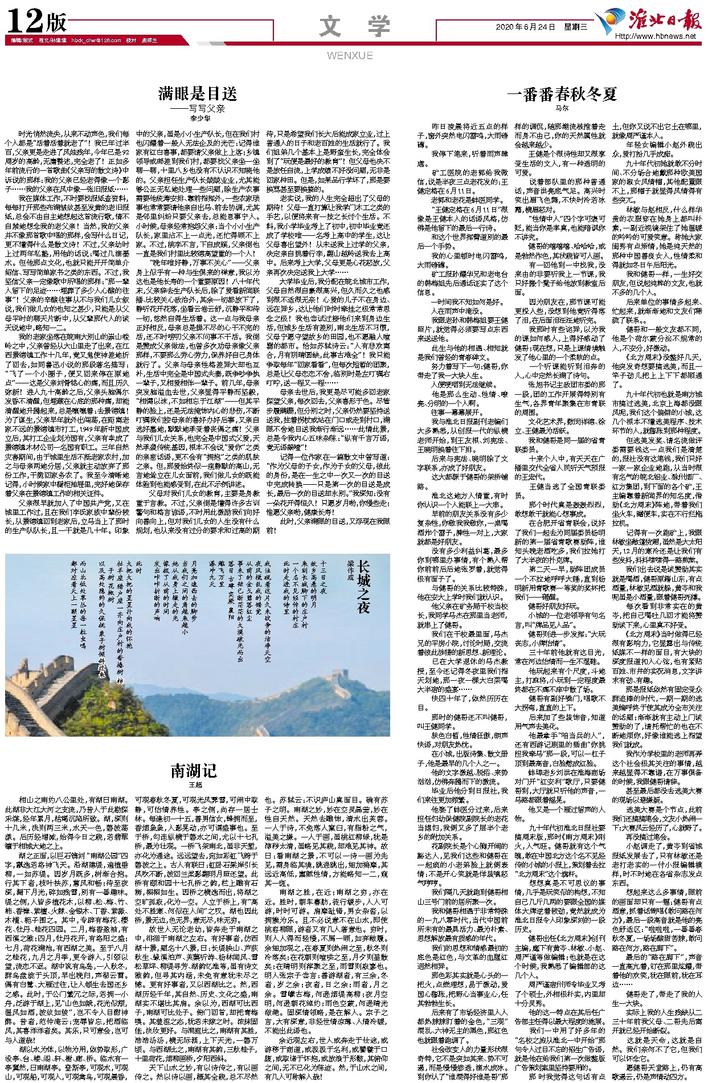李少华
时光悄然流失,从来不动声色,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着活着就老了”!我已年过半百,父亲更是走进了风烛残年,今年已是92周岁的高龄,无庸赘述,完全老了!正如多年前流行的一首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中诉说的那样: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我在媒体工作,不时要找报纸查资料,每每打开那些布满皱纹甚至发黄的老旧报纸,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首流行歌,情不自禁地想念我的老父亲!当然,我的父亲并不像那首歌中唱的那样,会写什么日记,更不懂得什么是散文诗!不过,父亲幼时上过两年私塾,用他的话说:喝过几滴墨水。但他那点文化,也就只能开开简单介绍信、写写简单家书之类的东西。不过,我坚信父亲一定像歌中所唱的那样:“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父亲的辛酸往事从不与我们儿女叙说,我们做儿女的也知之甚少,只能是从父母平时的聊天片断中,从父辈那代人的谈天说地中,略知一二。
我的老家坐落在皖南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中,父亲曾经从大山里走了出来,在江西景德镇工作十几年,竟又鬼使神差地折了回去,如同鲁迅小说的那段著名描写:“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这是父亲刻骨铭心的痛,而且历久弥新!进入九十高龄之后,父亲头脑偶尔发昏不清醒,但埋藏在心底的那种痛,却能清醒地升腾起来,总是嚷嚷着:去景德镇!为了谋生,父亲早年就外出闯荡,在距离老家不远的景德镇市打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其打工企业划为国有,父亲有幸成了景德镇木材公司一名国有职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城里生活不抵老家农村,加之与母亲两地分居,父亲就主动放弃了那份工作,干脆回家务农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家中橱柜抽屉里,完好地保存着父亲在景德镇工作的相关证件。
父亲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在城里工作过,且在我们李氏家族中辈份较长,从景德镇回到老家后,立马当上了那时的生产队队长,且一干就是几十年。印象中的父亲,虽是小小生产队长,但在我们村也闪耀着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光芒:记得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父亲做上上客;乡镇领导或邮差到我们村,都要找父亲坐一坐聊一聊,十里八乡也没有不认识不知晓他的。父亲担任生产队长兢兢业业,尤其能够公正无私地处理一些问题,除生产农事需要他统筹安排、靠前指挥外,一些农家琐事也常常要请他亲自出马、前去协调,尤其是邻里纠纷只要父亲去,总能息事宁人。小时候,母亲经常抱怨父亲:当个小小生产队长,家里沾不上一点光,还忙得顾不上家。不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父亲倒也一直是我们村里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个人!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父亲身上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禅意,我以为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八十年代末,父亲辞去生产队长后,除了爱看新闻联播、比较关心政治外,其余一切都放下了,静听花开花落,坐看云卷云舒,沉静平和待一切,悠然自得生活着。这一点与我母亲正好相反,母亲总是操不尽的心干不完的活,还不时唠叨父亲不问事不干活。我倒是赞成父亲做法,也曾多次劝母亲像父亲那样,不要那么劳心劳力,保养好自己身体就行了。父亲与母亲性格差异大却也互补,生活中完全是中国式夫妻,既争吵争执一辈子,又相爱相伴一辈子。前几年,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父亲显得平静而坚毅,“相儒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其平静的脸上,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悲伤,不断叮嘱我们按母亲的喜好办好后事,又亲自选好墓地,默默地承受着丧偶之痛!父亲与我们儿女关系,也完全是中国式父爱,天然承袭传统基因,根本不会说“爱你”之类的亲密话语,更不会有“拥抱”之类的肌肤之亲。但,那爱始终似一座静默的高山,无言地耸立在儿女面前,我们做儿女的既能体验到也能感受到,在此不示例讲述。
父母对我们儿女的教育,主要是身教重于言教。不过,父亲倒是懂得许多古训警句和格言谚语,不时用此激励我们向好向善向上,但对我们儿女的人生没有什么规划,也从来没有过分的要求和过高的期待,只是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成家立业,过上普通人的日子和老百姓的生活就行了。我们姐弟几个基本上是野蛮生长,完全体会到了“玩便是最好的教育”!但父母也决不是放任自流,上学成绩不好没问题,无非是回家种田。但是,如果品行学坏了,那是要挨骂甚至要挨揍的。
老实说,我的人生完全超出了父母的期待!父母一直打算让我学门木工之类的手艺,以便将来有一技之长讨个生活。不料,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初中毕业竟还成了学校唯一一名考上高中的学生,这让父母喜出望外!从未送我上过学的父亲,决定亲自挑着行李,翻山越岭送我去上高中。后来考上大学,父母更是心花怒放,父亲再次决定送我上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皖北城市工作,父母自然很自豪很高兴,但久而久之也感到很不适很无奈!心爱的儿子不在身边、远在异乡,这让他们时时牵挂之极常常思念之极!我也尝试过接他们来到身边生活,但城乡生活有差别,南北生活不习惯,父母宁愿守望故乡的田园,也不愿融入喧嚣的都市。恰如苏轼诗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只能争取每年“回家看看”,但每次短暂的团聚,总是让父母恋恋不舍,临别时是左叮嘱右叮咛,送一程又一程……
母亲去世后,我更是尽可能多回老家探望父亲,每次回去,父亲喜形于色。尽管步履蹒跚,但分别之时,父亲仍然要坚持送送我,拄着拐杖或站在门口或走到村口,满眼不舍地目送我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总是令我内心五味杂陈:“纵有千言万语,竟无语凝噎”!
记得一位作家在一篇散文中曾写道:“作为父母的子女,作为子女的父母,彼此的身份,是在一生之中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中完成转换——只是第一次的目送是成长,最后一次的目送却永别。”我深知:没有一朵花开得恒久!只愿岁月哟,你慢些走;惟愿父亲哟,健康长寿!
此时,父亲满眼的目送,又浮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