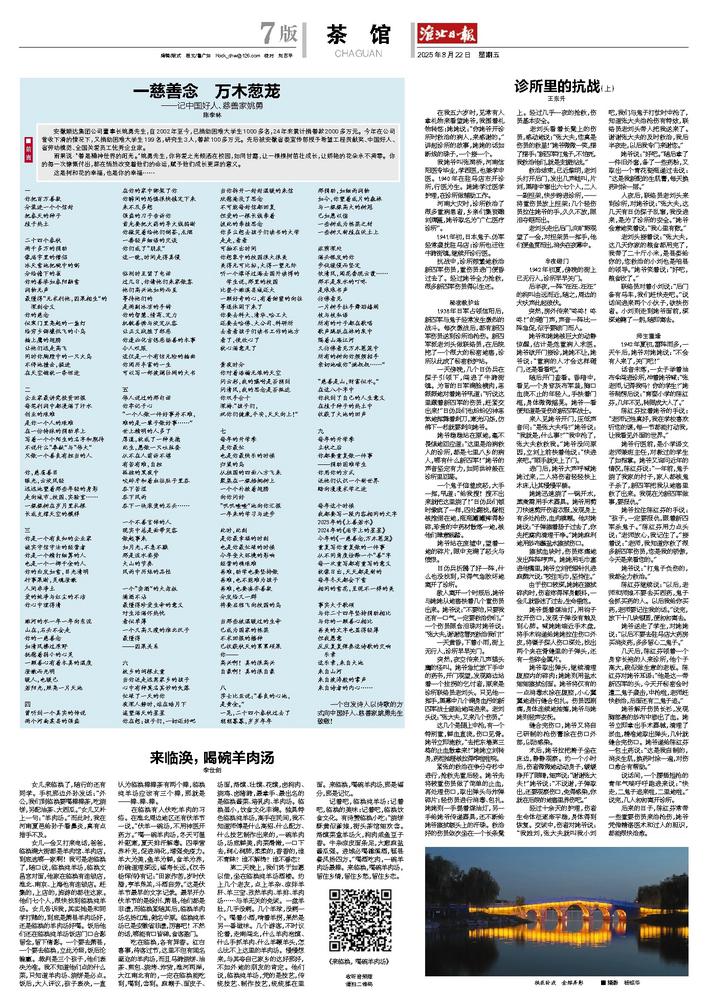王东升
在我五六岁时,见常有人拿礼物来看望姥爷,我围着礼物转悠;姥姥说:“你姥爷开诊所时救治的病人,来感谢的。”讲起诊所的故事,姥姥的话如断线的珠子,一个接一个。
我姥爷叫张洞桥,河南信阳医专毕业,学西医,也兼学中医。1940年在驻马店市开诊所,行医为生。姥姥学过医学护理,在诊所做辅助工作。
河南大灾时,诊所救治了很多重病患者,乡亲们集资雕刻牌匾,姥爷取名为“广仁医疗诊所”。
1941年初,日本鬼子、伪军经常袭扰驻马店;诊所也迁往牛蹄街镇,继续开诊行医。
抗战中,诊所频繁地救治新四军伤员,重伤员进门便昏过去了。经过姥爷全力抢救,很多新四军伤员得以生还。
秘密救护站
1938年日军占领信阳后,新四军与鬼子经常发生激烈的战斗。每次激战后,都有新四军伤员送到诊所治枪伤。新四军派老刘头做联络员,在后院挖了一个很大的秘密地窖,诊所从此成了秘密救护站。
一天傍晚,几个日伪兵在探子引领下,闯进了牛蹄街镇。为首的日军满脸横肉,恶狠狠地对着姥爷吼道:“听说这里藏着新四军的伤员,赶紧交出来!”日伪兵们也纷纷凶神恶煞地挥舞着刺刀,寒光闪烁,仿佛下一秒就要刺向姥爷。
姥爷稳稳站在原地,毫不畏惧地回应道:“这里是治病救人的诊所,都是七里八乡的病人,哪有什么新四军!”姥爷的声音坚定有力,如同洪钟般在诊所里回荡。
一个鬼子恼羞成怒,大手一挥,吼道:“给我搜!搜不出来就把这里烧了!”日伪兵们顿时像疯了一样,四处翻找,橱柜被推倒在地,瓶瓶罐罐摔得粉碎,珍贵的中药材散落一地,被他们肆意践踏。
姥爷站在废墟中,望着一地的碎片,眼中充满了怒火与愤恨。
日伪兵折腾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找到,只得气急败坏地离开了诊所。
敌人离开一个时辰后,姥爷与姥姥从地窖扶着几个重伤员出来。姥爷说:“不要怕,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定要救治你们。”一个伤员眼含泪珠对姥爷说:“张大夫,谢谢您冒死救治我们!”
一天黄昏,下着小雨,街上无行人,诊所早早关门。
突然,夜空传来几声猫头鹰的怪叫。姥爷急忙放下手中的药书,开门观望,发现路边站着一个拄拐的乞讨者,原来是诊所联络员老刘头。只见他一挥手,黑幕中几个满身血污的新四军战士踉跄地闯进来。老刘头说:“张大夫,又来几个伤员。”
这几个是腿上中枪,有一个特别重,鲜血直流,伤口见骨。姥爷立即施救,“去把东墙第三格的止血散拿来!”姥姥立刻转身,药柜抽屉被拉得哗啦啦响。
紧张的救治在争分夺秒中进行,抢救先重后轻。姥爷先将较重伤员做了简单的止血,再处理伤口,取出弹头与炸弹碎片;轻伤员进行消毒、包扎。姥姥则一手提着煤油灯,另一手给姥爷传递器具,还不断给姥爷擦拭额头上的汗珠。救治好的伤员依次坐在一个长条凳上。经过几乎一夜的抢救,伤员基本安全。
老刘头看着长凳上的伤员,感动地说;“张大夫,您真是伤员的救星!”姥爷微微一笑,摆了摆手:“新四军打鬼子,不怕死,我救治他们,就是支援抗战。”
救治结束,已近黎明,老刘头打开后门,发出几声蛙叫,片刻,黑暗中窜出六七个人,二人一副担架,快步跨进诊所,一一将重伤员放上担架;几个轻伤员拉住姥爷的手,久久不放,眼泪夺眶而出。
老刘头走出后门,向旷野观望了一会,对担架员一挥手,他们便鱼贯而出,消失在夜幕中。
半夜砸门
1942年初夏,傍晚的街上已无行人,诊所早早关门。
后半夜,一阵“汪汪、汪汪”的狗叫由远而近,随之,周边的犬吠声此起彼伏。
突然,房外传来“咚咚!咚咚!”的砸门声,声音一阵比一阵急促,似乎要破门而入。
姥爷和姥姥被巨大的动静惊醒,估计是危重病人求医。姥爷欲开门接诊,姥姥不让,姥爷说:“重病的人才会这样砸门,还是看看吧。”
随后开门查看。昏暗中,看见一个身穿灰布军装,胸口血流不止的年轻人,手扶着门框,身体微微摇晃。姥爷一看便知道是受伤的新四军战士。
来人见姥爷开门,压低声音问:“是张大夫吗?”姥爷说:“我就是,什么事?”“我中枪了,张大夫救救我。”姥爷没问原因,立刻上前扶着他说:“快进来吧。”顺手就关上了门。
进门后,姥爷大声呼喊姥姥过来,二人将伤者轻轻扶上木床,让其慢慢平躺。
姥姥迅速烧了一锅开水,蒸煮需用手术器具。姥爷用剪刀快速剪开伤者衣服,发现身上有多处枪伤,血肉模糊。他对姥姥说:“子弹擦着肠子过去了,你先把腐肉清理干净。”姥姥麻利地用纱布蘸盐水擦拭伤口。
擦拭血块时,伤员疼痛地发出阵阵哼声。姥姥用毛巾塞进他嘴里,姥爷立刻把银针扎进麻醉穴说:“咬住毛巾,坚持住。”
由于伤口较深,姥姥在擦拭碎肉时,伤者疼得浑身颤抖,一会儿就昏迷了过去,生命垂危。
姥爷提着煤油灯,用钩子拉开伤口,发现子弹没有触及到心肺。喊姥姥端近手术盘,将手术钩递给姥姥拉住伤口外皮,将镊子探入伤口深处,找出两个夹在骨缝里的子弹头,还有一些碎金属片。
姥爷取出弹头,继续清理腹腔内的碎肉;姥姥则用盐水细细擦拭创面。姥爷将仅有的一点消毒水涂在腹腔,小心翼翼地进行缝合包扎。伤员因剧痛,身体连续地抽搐,姥爷与姥姥则轻声安抚。
缝合完伤口,姥爷又将自己研制的枪伤膏涂在伤口外部,以防感染。
术后,姥爷拉把椅子坐在床边,静静观察。约一个小时后,伤者微微地动动身子,缓缓睁开了眼睛,细声说:“谢谢张大夫!”姥爷说:“不说谢,子弹取出,还要观察伤口,免得感染,你就在后院的地窖里养伤吧。”
经过十余天的护理,伤者生命体征逐渐平稳,身体得到恢复。交谈中,伤者对姥爷说:“我姓刘,张大夫就叫我小刘吧,我们与鬼子打仗时中枪了,知道张大夫治枪伤有特效,联络员老刘头带人把我送来了。谢谢张大夫的及时救治,我后半夜走,以后我专门来谢您。”
姥爷说:“好吧。”随后拿了一件旧外套,备了一些药粉,又取出一个青花瓷瓶递过去说:“这是我新配的生肌膏,每天换药时涂一层。”
入夜后,联络员老刘头来到诊所,对姥爷说:“张大夫,这几天有日伪探子乱窜,我没进来,是为了诊所的安全。”姥爷会意地笑着说:“我心里有数。”
老刘头接着说:“张大夫,这几天你家的粮食都用完了,我带了二十斤小米,是县委给你的,您救治的小刘也是咱县的领导。”姥爷笑着说:“好吧,粮食收了。”
联络员对着小刘说:“后门备有马车,我们赶快走吧。”说话间进来两个小伙子,欲扶伤者。小刘则走到姥爷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即离去。
师生重逢
1942年夏初,雷阵雨多,一天午后,姥爷对姥姥说:“不会有人来了,关门吧!”
话音未落,一女子举着油布伞闯进诊所,冲着姥爷喊:“张老师,记得我吗?你的学生?”姥爷稍愣后说:“育婴小学的陈红芬,几年不见,转眼成大人了。”
陈红芬拉着姥爷的手说;“老师记性真好,我在学校喜欢听您的课,每一节都能打动我,让我看见外面的世界。”
姥爷行医前,是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对教过的学生了如指掌。姥爷又询问近年的情况,陈红芬说:“一年前,鬼子烧了我家的村子,家人都被鬼子杀了,新四军把我从地窖里救了出来。我现在为新四军做事,要报仇。”
姥爷拉住陈红芬的手说:“孩子,一定要报仇,跟着新四军杀鬼子。”陈红芬用力点头说:“老师放心,我记住了。”接着说:“老师,我知道你救了很多新四军伤员,您是我的骄傲,今天是来看您的。”
姥爷说:“打鬼子负伤的,我都全力救治。”
陈红芬继续说:“以后,老师和师娘不要去买西药,鬼子会抓买药的人。以后我给你买药,老师要记住我的话。”说完,放下十几块银圆,便匆匆离去。
姥爷送走了学生,对姥姥说:“以后不要去驻马店大药房买消炎药,多多留心二鬼子。”
几天后,陈红芬领着一个身穿长袍的人来诊所,他个子高大,貌似做生意的老板。陈红芬对姥爷耳语:“他是这一带新四军的头,今天开秘密会时遭二鬼子袭击,中枪啦,老师赶快救治,后面还有二鬼子追。”
姥爷解开伤员长衫,发现胸部裹的纱布中渗出了血。姥爷立即拿出手术器械,清理了淤血,精准地取出弹头,几针就缝合完伤口。姥爷递给陈红芬一包土药说:“这是我自制的,消炎生肌,换药时涂一遍,对伤口愈合有帮助。”
说话间,一个腰插短枪的青年气喘吁吁跑进来说:“快走,二鬼子追来啦,二里地啦。”说完,几人匆匆离开诊所。
后来的日子,陈红芬常带一些重要伤员来治枪伤,姥爷凭借精湛医术和过人的胆识,都能很快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