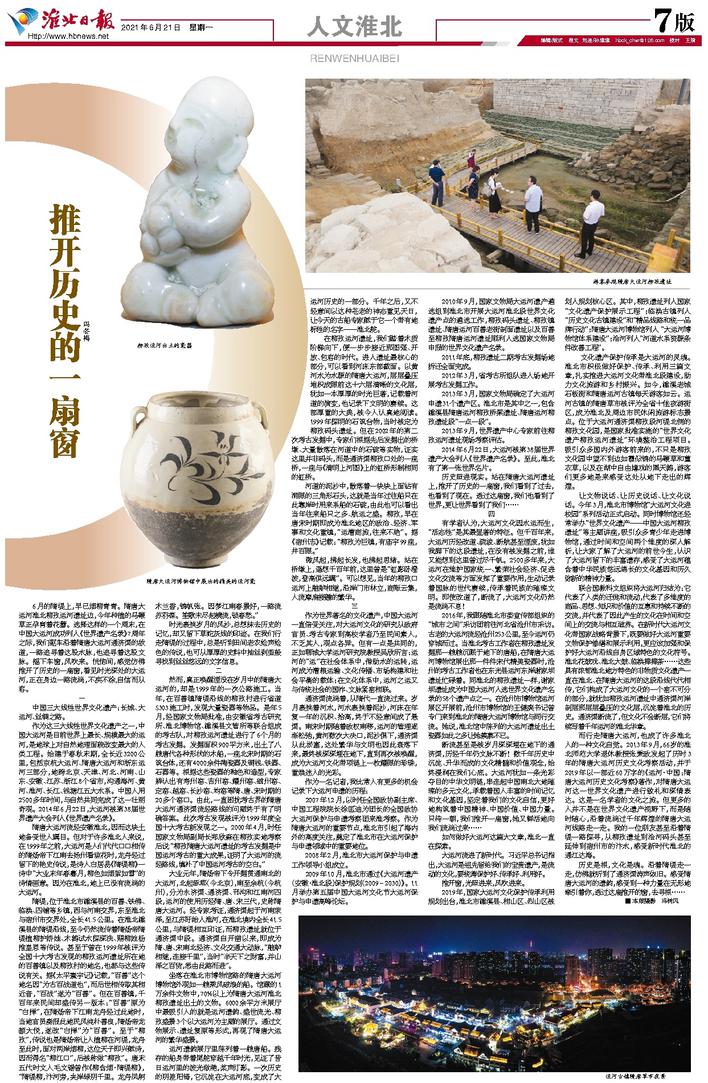冯冬梅
6月的隋堤上,早已烟柳青青。隋唐大运河淮北柳孜运河遗址边,今年种植的马鞭草正孕育着花蕾。选择这样的一个周末,在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周年之际,我们驱车沿着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故道,一路追寻着这股水脉,也追寻着这股文脉。摇下车窗,风吹来。恍惚间,感觉仿佛推开了历史的一扇窗,看见时光深处的大运河,正在身边一路流淌,不疾不徐,自信而从容。
一
中国三大线性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
作为这三大线性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大运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是地球上对自然地理面貌改变最大的人类工程。始建于春秋末期,全长近3200公里,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中国人用2500多年时间,与自然共同完成了这一壮丽奇观。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被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隋唐大运河流经安徽淮北,因而这块土地备受世人瞩目。但对于许多淮北人来说,在1999年之前,大运河是人们代代口口相传的隋炀帝下江南去扬州看琼花时,龙舟经过留下的艳史传说,是诗人白居易《隋堤柳》一诗中“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的诗情画意。因为在淮北,地上已没有流淌的大运河。
隋堤,位于淮北市濉溪县的百善、铁佛、临涣、四铺等乡镇,西与河南交界,东至淮北与宿州市交界处,全长41.5公里。在淮北濉溪县的隋堤沿线,至今仍然流传着隋炀帝隋堤植柳护娇娃、木鹅试水探深浅、赐柳姓杨推皇恩等传说。甚至于曾在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柳孜运河遗址所在地的百善镇以及柳孜村的地名,也都与这些传说有关。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百善”这个地名因“为古百战道也”,而后世相传取其相近音,“百战”遂为“百善”。但在百善镇,千百年来民间却盛传另一版本:“百善”原为“白掸”,在隋炀帝下江南龙舟经过此地时,当地官员奏报此地民风纯朴善良,隋炀帝龙颜大悦,遂改“白掸”为“百善”。至于“柳孜”,传说也是隋炀帝让人植柳在河堤,龙舟至此时,面对两岸烟柳,这位天子即兴赋诗,因而得名“柳江口”,后被称做“柳孜”。唐末五代时文人毛文锡曾作《柳含烟·隋堤柳》,“隋堤柳,汴河旁,夹岸绿阴千里。龙舟凤舸木兰香,锦帆张。因梦江南春景好,一路流苏羽葆。笙歌未尽起横流,锁春愁。”
时光裹挟岁月的风沙,总想抹去历史的记忆,却又留下草蛇灰线的印迹。在我们行走隋堤的过程中,总是听到田间老农绘声绘色的传说,也可从厚厚的史料中抽丝剥茧般寻找到丝丝悠远的文字信息。
二
然而,真正唤醒湮没在岁月中的隋唐大运河的,却是1999年的一次公路施工。当年,在百善镇隋堤沿线的柳孜村进行省道S303施工时,发现大量瓷器等物品。是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淮北博物馆、濉溪县文管所等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柳孜运河遗址进行了6个月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出土了八艘唐代各种形状的木船,一座北宋时期的石筑台体,还有4000余件陶瓷器及铜钱、铁器、石器等。根据这些瓷器的釉色和造型,专家辨认出有寿州窑、吉州窑、耀州窑、磁州窑、定窑、越窑、长沙窑、均窑等隋、唐、宋时期的20多个窑口。由此,一直困扰考古界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流经路线的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答案。此次考古发现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0年4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在柳孜实地考察后说:“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运河考古的重大成果,证明了大运河的流经路线,填补了中国运河考古的空白。”
大业元年,隋炀帝下令开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运河的使用历经隋、唐、宋三代,史称隋唐大运河。经专家考证,通济渠起于河南荥泽,至江苏盱眙入淮河,在淮北境内全长41.5公里,与隋堤相互印证,而柳孜遗址就位于通济渠中段。通济渠自开凿以来,即成为隋、唐、宋南北经济、文化交通大动脉,“舳舻相继,连接千里”,当时“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坐落在淮北市博物馆路的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外观如一艘乘风破浪的船。馆藏的1万余件文物中,70%以上为隋唐大运河淮北柳孜遗址出土的文物。6000余平方米展厅中最吸引人的就是运河遗韵、盛世流光、柳孜盛景3个以大运河为主题的展厅。通过文物展示、遗址复原等形式,再现了隋唐大运河的繁华盛景。
运河遗韵展厅里陈列着一艘唐船。残存的船身带着尾舵穿越千年时光,见证了昔日运河里的波光潋滟,桨声灯影。一次历史的阴差阳错,它沉淀在大运河底,变成了大运河历史的一部分。千年之后,又不经意间以这种苍老的神态重见天日,让今天的古船专家赋于它一个带有地标性的名字——淮北舵。
在柳孜运河遗址,我们踏着木质阶梯向下,便一步步接近那图强、开放、包容的时代。进入遗址最核心的部分,可以看到河床东部截面。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隋唐大运河,层层叠压堆积成眼前这十六层清晰的文化层,犹如一本厚厚的时光巨著,记载着河道的演变,也记录下文明的赓续。这部厚重的大典,被今人认真地阅读。1999年探明的石筑台物,当时被定为柳孜码头遗址。但在2002年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专家们根据先后发掘出的桥墩、大量散落在河道中的石碇等实物,证实这里并非码头,而是通济渠柳孜口处的一座桥,一座与《清明上河图》上的虹桥形制相同的虹桥。
河道的泥沙中,散落着一块块上面钻有洞眼的三角形石头,这就是当年过往船只在此靠岸时用来系船的石碇,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往来船只之多、航运之盛。柳孜,早在唐宋时期即成为淮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据《宿州志》记载:“柳孜为巨镇,有庙宇99座,井百眼。”
微风起,拂起长发,也拂起思绪。站在桥墩上,遥想千百年前,这里曾是“虹影卧澄波,登高供远瞩”。可以想见,当年的柳孜口运河上舳舻相继,沿岸门市林立,商贩云集,人流摩肩接踵的繁华。
三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一直倍受关注,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从政府官员、考古专家到高校学者乃至民间素人,不乏其人,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正如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教授吴欣所言:运河的“运”在社会体系中,借助水的运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联。
通济渠流淌着,从隋代一直流过来。岁月裹挟着河水,河水裹挟着泥沙,河床在年复一年的沉积、抬高,终于不经意间成了悬渠。南宋时期随着政权南移,运河的管理逐渐松弛,黄河数次大决口,泥沙俱下,通济渠从此淤塞,这处繁华与文明也因此衰落下来,最终被深深埋在地下,直到再次被唤醒,成为大运河文化带项链上一枚耀眼的珍珠,重焕迷人的光彩。
作为一名记者,我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记录下大运河申遗的历程:
2007年12月,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为团长的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来淮考察。作为隋唐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淮北市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奠定了淮北市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2008年2月,淮北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2009年10月,淮北市通过《大运河遗产(安徽·淮北段)保护规划(2009-2030)》。11月举办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
2010年9月,国家文物局大运河遗产遴选组到淮北市开展大运河淮北段世界文化遗产点的遴选工作,柳孜码头遗址、柳孜镇遗址、隋唐运河百善老街剖面遗址以及百善至柳孜隋唐运河遗址顺利入选国家文物局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底,柳孜遗址二期考古发掘场地拆迁全面完成。
2012年3月,省考古所组队进入场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确定了大运河申遗31个遗产区。淮北市是其中之一,包含濉溪县隋唐运河柳孜桥梁遗址、隋唐运河柳孜遗址段“一点一段”。
2013年9月,世界遗产中心专家前往柳孜运河遗址现场考察评估。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被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淮北有了第一张世界名片。
历史照进现实。站在隋唐大运河遗址上,推开了历史的一扇窗,我们看到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透过这扇窗,我们也看到了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了我们……
四
有学者认为,大运河文化因水运而生,“活态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但千百年来,大运河历经改道、疏浚、断航甚至湮废,犹如我脚下的这段遗址,在没有被发掘之前,谁又能想到这里曾过尽千帆。2500多年来,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社会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动记录着国脉的世代赓续,传承着民族的璀璨文明。即使改道了,断流了,大运河文化仍然是流淌不息!
2016年,我跟随淮北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城市之间”采访团前往河北省沧州市采访。古老的大运河流经沧州253公里,至今运河仍穿城而过。当淮北考古工作者在柳孜遗址发掘那一艘艘沉眠于地下的唐船,在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展出那一件件宋代精美瓷器时,沧州的考古工作者也在东光县运河东岸谢家坝遗址忙碌着。同淮北的柳孜遗址一样,谢家坝遗址成为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58个遗产点之一。在沧州市博物馆运河展区开展前,沧州市博物馆的王健爽书记曾专门来到淮北的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与同行交流。她说,淮北馆中陈列的大运河遗址出土瓷器如此之多让她羡慕不已。
断流甚至是被岁月深深埋在地下的通济渠,历经千年仍文脉不断!数千年历史中沉淀、升华而成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始终浸润在我们心底。大运河犹如一条光彩夺目的中华文明链,串连起中国南北大地璀璨的多元文化,承载着国人丰富的时间记忆和文化基因,坚定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好地构筑着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只待一朝,我们推开一扇窗,她又鲜活地向我们流淌过来……
如何做好大运河这篇大文章,淮北一直在探索。
大运河流进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推开窗,光照进来,风吹进来。
2019年,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出台,淮北市濉溪县、相山区、烈山区被划入规划核心区。其中,柳孜遗址列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工程”;临涣古镇列入“历史文化古镇建设”和“精品线路和统一品牌行动”;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列入 “大运河博物馆体系建设”;浍河列入“河道水系资源条件改善工程”。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大运河的灵魂。淮北市积极做好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淮北段建设,助力文化旅游和乡村振兴。如今,濉溪老城石板街和隋唐运河古镇每天游客如云。运河古镇的隋唐草市被评为全省十佳夜游街区,成为淮北及周边市民休闲旅游标志景点。位于大运河通济渠柳孜段河堤北侧的柳孜文化园,是国家批准实施的“世界文化遗产柳孜运河遗址”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的,不只是柳孜文化园中望不到边如霞似锦的马鞭草和薰衣草,以及在湖中自由嬉戏的黑天鹅,游客们更多地是来感受这处从地下走出的辉煌。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今年3月,淮北市博物馆“大运河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同时博物馆还经常举办“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柳孜遗址”等主题讲座,吸引众多青少年走进博物馆,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深入解析,让大家了解了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认识了大运河留下的丰富遗存,感受了大运河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和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运河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在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战略背景下,既要做好大运河重要文物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更应该加强和保护好大运河沿线自身区域特色的文化符号。淮北花鼓戏、淮北大鼓、临涣棒棒茶……这些具有浓郁淮北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在淮北、在隋唐大运河的这段沿线代代相传,它们构成了大运河文化的一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就犹如柳孜运河遗址中通济渠河岸剖层那层层叠压的文化层,沉淀着淮北的历史。通济渠断流了,但文化不会断层,它们将续写着千年运河的淮北华章。
而行走隋唐大运河,也成了许多淮北人的一种文化自觉。2013年9月,66岁的淮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张秉政发起了历时3年的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活动,并于2019年以一部近60万字的《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著作,对隋唐大运河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进行致礼和深情表达。这是一名学者的文化之旅。但更多的人并不是在世界文化遗产视野下,而是随时随心,沿着流淌过千年辉煌的隋唐大运河线路走一走。我的一位朋友甚至沿着隋堤一路探寻,从柳孜遗址到浍河码头甚至延伸到宿州市的汴水,感受新时代淮北的通江达海。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沿着隋堤走一走,仿佛就听到了通济渠涛声依旧。感受隋唐大运河的遗韵,感受到一种力量在无形地牵引着你,透过这扇推开的窗,去寻根……
■ 本版摄影 冯树风